(文/姜羽桐)“企业经营风险完全转化为个人财务风险,创新动力必然受损;万一创业失败,创业者一辈子翻不了身。”“作为基金管理人需要对LP负责,必须行使回购权,否则我就要成为被告。”就创业者与投资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集微网在“芯片投资对赌困局系列”的前两篇调查文章《创始人踩雷实录:当造芯理想撞上对赌铁幕》《连环爆雷,半导体投资机构的两难抉择》已做深入剖析,引发业界就对赌协议使用不当、过度使用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广泛思考。
今天,“对赌协议” “回购条款” 作为普遍性问题,其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各方不止围绕契约效力、风险转嫁与商业伦理等展开博弈,司法判例的调整、法律观点的分歧,更让这场旷日持久的角力充满复杂性。自去年以来,半导体行业触发对赌而引起的诉讼案已频频出现,创业者与投资人对簿公堂的案例不在少数。当资本与创新“反目”,通力合作演变为同室操戈的战争,困在“对赌官司”里的人,何去何从?
对赌背离初衷,IC回购起潮
尽管“对赌回购”在国内大行其道,但在起源地的欧美国家却日渐式微,美国硅谷仅25%的创业企业在吸纳投资时使用了该条款。复旦大学教授张巍编写的《资本的规则》一书中,就有一篇文章叫作《硅谷无对赌》,专门论证了美国投资人“不感冒”对赌的一系列原因。
在国内,对赌初始阶段仍致力于弥合投资方、融资方的分歧,对双方设定了义务与权利。譬如,蒙牛2003年通过“对赌协议”获得摩根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并于次年在香港主板上市,摩根等机构投资者获得巨大收益,双方实现共赢。
但随着投资环境、风险的变化,对于对赌存在的意义,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叶臻勇律师表示,对赌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业项目退出渠道被严重堵塞。随着A股IPO阶段性收紧,以及香港(中国)、美国等境外证券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投资机构找不到退出的理想途径,“还有次理想方案,譬如借壳上市、并购退出等,但这些更加考验市场投资者的热情,在整体观望的情绪下,投资机构往往倾向通过对赌回购脱身。”
礼丰律师事务所发布的《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显示,检索沪深交易所2023年受理的项目发现,成功申报IPO的企业,约65%设置回购权条款(未递交申请的创业企业中,比例或更高);汉坤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在《PE/VC项目数据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境内投资事件中设置有回购权条款的超过90%——而在回购条件设置上,投资人一般在要求回购人承担回购义务时,会附加较高的年化资金收益,且普遍高于同期的市场资金成本,以6%~8%较为常见,更夸张者能高达20%;投资人还会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联合创始人等,对此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或直接要求实际控制人作为回购义务人。
刚开始,未约定明确回购期限的案例占了多数,这是由于创业者、投资人对约定行权期限比较谨慎,企业担心条款会促使投资人在权利期限内尽快行权,投资人则会担心超过期限没有行使回购权利可能导致权利丧失。
直至202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没有约定回购期限的情形作出“以不超过6个月为宜”的表态,事态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有投资人表示,将推动未约定回购期限的增加补充约定,对已具有行权条件的正考虑是否发行权通知。本想缓解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矛盾的“良药”,却朝着反方向疾驰。更为严峻的是,早先处于弱势地位的创业者,缺少对不利条款说“No”的资格,当大面积“回购潮”降临,他们被迅速拽入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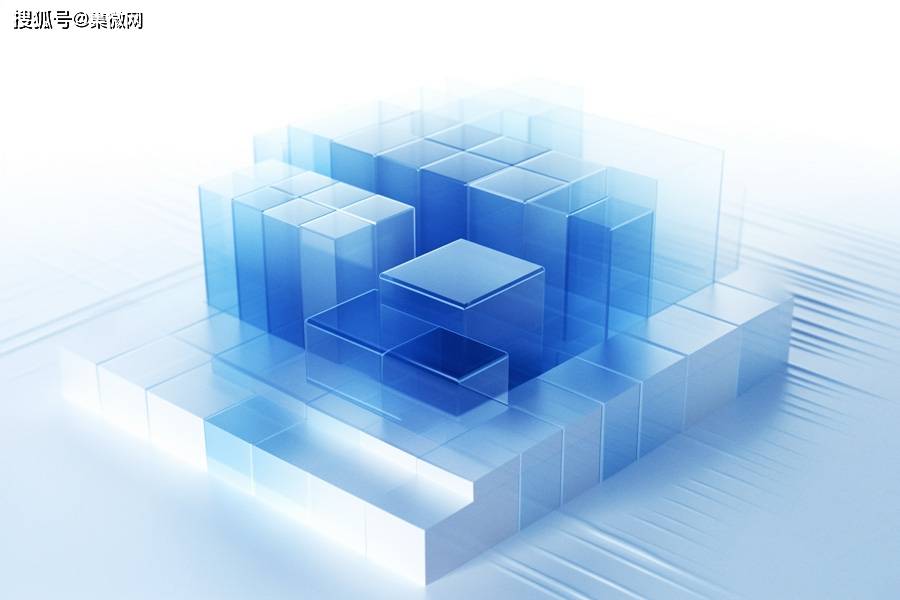
有产业人士指出,2019—2022年是我国半导体投资的火热期,“对赌回购”在该领域造成的冲击尤甚。当年不在少数的投资机构为提早卡位某细分赛道,在没有时间做好尽调的情况下,抢着投、找关系投,将“对赌协议”视作对投资时高估值的回拨机制;同时,一部分半导体“泡沫”急于拿到投资,更加忽视对赌后果的严重性,大量签订IPO“对赌协议”,并在今年底就将到期。
针对上述乱象,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曾公开批评:“一些投资人认为只要上市就能赚钱,干脆连业绩对赌都省了,直接做上市对赌,把往往多年后才会触发的不上市就回购,和以一两年经营指标做估值对赌,将两个不同的物种合二为一,变成短时间即触发的上市对赌。”
“无效”认定难,握手即异梦
美国硅谷公司法律师XIAOXIAO LIU曾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加州的一个案件诉讼中,法院根本不考虑“对赌协议”的效力。既然对赌在国内出现诸多弊端,且作为普遍性问题,依靠倡议难以解决问题,由法院判定“对赌无效”是否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叶臻勇律师向集微网介绍,的确有法律界人士朝着这一方向在努力,包括最近也出现一些司法案例是这样判决的,在一审的时候被认定为“明股实债”而判定无效(但二审又被推翻了)。
“但是,从法律层面直接宣布‘对赌无效’过于理想,不太可能因为创业者单方面的忧虑而禁止;同时,对赌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情况(有可能它们企业的经营透明度更高,项目可预期性更好,市场资金也更充裕等),真正应当警惕并加以限制的是‘对赌回购’被滥用的现象。”叶臻勇律师特别强调。
事实上,近年司法裁判中“对赌协议”被认定无效,以及投资行为被认定不构成对赌的几个代表性判例均较为特殊——滥用股东权利、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回购条款无效;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对赌回购条款无效;“新三板”挂牌应当清理的抽屉对赌协议无效等。这些案例对于半导体产业存在的“对赌”困境并不具有太多参考意义,更遑论用作支持“对赌无效”的论据了。

在国内,涉及“对赌协议”有效性的司法实践经历了相当长的探索,从无效论、到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目标公司股东或实控人对赌有效,再到与目标公司对赌有效但实际履行主张不一定被支持的认识历程,主要脉络由2012年“海富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2023年《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等一并串起。
简言之,“海富案”确立了“与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规则,随后导致投资机构普遍要求创始人个人承担回购责任;《九民纪要》虽承认与公司对赌的效力,但要求履行减资程序,实际操作困难。《九民纪要》发布后,对于目标公司未经减资程序而投资人请求目标公司实际履行回购的情形,法院基本都判决予以驳回。这反而更加坚定了投资机构将实控人,包括创始股东纳入回购义务主体的决心,并在一开始就坚定执行。
吊诡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面对创业项目,部分投资人在获得回购条款后,便放心不管;创业者签字之前,就有了谋求保存个人财产的动机。双方几乎在握手的同时就已同床异梦,更可怕的是,直至“对簿公堂”才发现“对赌回购”这一承诺的兑现存在极大变数,就连官司也不太好打。“我国早期的对赌案件裁决非常混乱,尽管《九民纪要》对裁判标准实现初步统一,但从法律层面而言,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就“对赌回购”形成完全统一或者权威的定性。”叶臻勇律师说道。
貌合神离,困在“对赌”里的人
当“对赌回购”成了催命符,投资机构转向寻求创始人回购并承担连带责任。根据礼丰律师事务所统计的回购争议案件中,大约90%的案件,投资机构会将创始人列为被告或共同被告,法院支持投资机构回购诉请占比大约在82.39%。此外,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案件中,平均执行回款率仅为约6%;进入执行程序的回购案件,100%回款并执行完毕的案件仅占约4.6%。
一般来说,公司没能按期上市或实现盈利的背后,有政策更迭和经营不善等诸多因素,现金流往往已经出现问题。投资人受LP委托,必然要求回购,难免使得公司状况雪上加霜。而创始人为了避免惨烈后果,即便违背初衷,也只有采取“掏空公司”“资产隔离”,甚至“跨境配置”等措施,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从结果看,绝大部分情形下都是双输的结局。长期与股权机构和科技企业打交道的证券机构人士提醒,创业者在面临触发“对赌回购”风险时,要积极与投资机构沟通,避免走到诉讼仲裁那一步,推动企业在国内主板、科创板或北交所上市,甚至到香港上市都可以考虑,尽量通过磋商机制解决问题,“我相信投资机构也不愿意走到上法庭那一步,只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资机构必须有动作和留痕;投资机构也面临LP(出资人)的压力。”
此外,身处市场格局大变、A股IPO阶段性收紧的当下,投融资双方已到了必须正视“对赌回购”合理性的时候。邝子平认为:“对赌条款不是不可用,但应该是在个别的情况下使用,比如对相对成熟的企业,对比较固定的商业模式、发展路径,在小范围内通过对赌做一些估值的调节不是不可,但成为项目标配绝对不应该。”

在政策端,国内也出现调整趋势。2024年9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尽快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卡点……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为打破国资创投与市场化投资机构之间愈发突出的矛盾,地方政府方面,广东提出“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来考核国有天使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四川、安徽也都提出不同程度的容错政策。
有产业人士指出,对赌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是不是可以探索在协议中附加一些限定条件?既激励公司股东勤勉创业,也监督其弄虚作假等不合规行为。倘若因政策环境变化等商业风险导致的企业经营不善,则由创业者和投资机构风险共担。
“要真正解决对赌问题,还要上升到立法层面。”叶臻勇律师强调,对赌在促进产业创新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对于风险投资、私募投资行业中存在的滥用对赌回购、刚性兑付、明股实债等现象,一定要给予严重关注;此外,目前大量对赌案件并不是在法院层面解决的,而是通过仲裁路径,这需要国家出台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导整个过程规范。一旦有了立法,不仅国内的对赌诉讼仲裁有了依据,甚至国外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想在我国法院得到执行也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让“带着脚镣跳舞”的对赌发挥更大作用。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